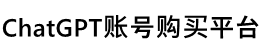王迁:ChatGPT生成的内容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先做个广告:如需代注册帐号或代充值Chatgpt Plus会员,请添加站长客服微信:muhuanidc
ChatGPT生成的内容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王迁|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转载对注释与参考文献进行了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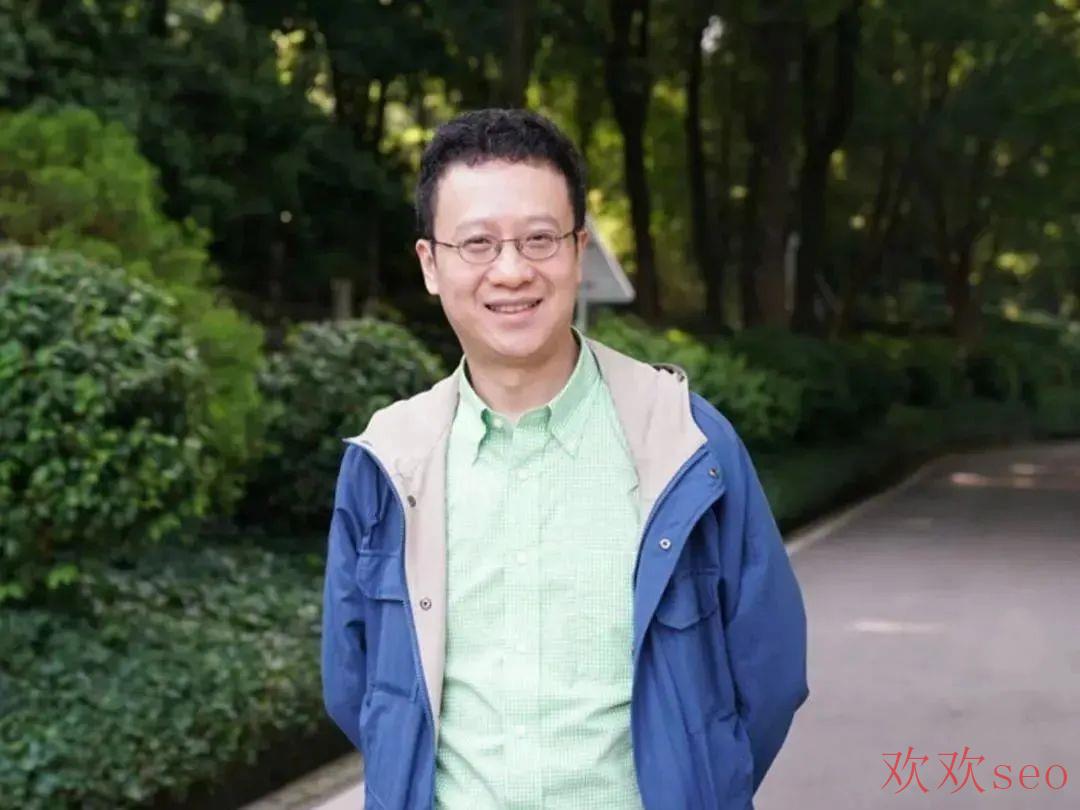
王迁教授
根据测试的结果,笔者将ChatGPT定位为“智能搜索引擎+智能文本分析器+智能洗稿器”。之所以称为“智能搜索引擎”,是由于如果该问题在互联网中存在直接相关的信息,则ChatGPT会找到这些信息,而且极可能在算法中包括对权重的衡量,即如果搜索到的信息很多,ChatGPT会根据一些指标(如作者的职称或所在机构的排名等)进行排序,较多地提取排序在前的信息。如果没法搜索到直接相关的信息。ChatGPT就会退而求其次,搜索与之有一定关联性的信息,而不是直接放弃。说它是“智能文本分析器”,是由于ChatGPT会对搜索出的海量信息进行梳理总结,提取公因数,将相同观点和区别观点归纳出来。比如其搜索到的文章虽然有100篇之多,但针对发问一共就提出了三种观点,ChatGPT就可以够将这三种观点提炼出来。与此同时,ChatGPT或者“智能洗稿器”。通过测试发现,ChatGPT即便搜索出了与问题直接相关的信息,也不会直接将文字内容粘贴过来,而是会进行同义词替换,也就是以区别的文字组合、遣辞造句表达相同的观点。

有关ChatGPT对文学、教育、伦理和哲学等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讨论。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是,ChatGPT生成的内容会不会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智能搜索”“智能文本分析”和“智能洗稿”这三种功能在ChatGPT中的有机结合,在进程和结果上都已高度近似人类对文字的撰写。当一名法学本科生被要求对问题作出专业回答时,也需要先查阅相关文献,对文本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在不能提出新观点的情况下,也会用自己的语言重述其总结出的观点。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须为人类的创作成果
对此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包括ChatGPT产在内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情势上的“独创”,其实不是构成作品的充分条件。对此可以罗列“猕猴自拍照案”予以说明。一名英国摄影师在印尼拍猕猴的时候,一只猕猴抢过照相机,模仿摄影师的动作按快门,机缘偶合拍出了一张自拍照。摄影师抢回相机以后将自拍照传给朋友看,该朋友又将照片上传到网上,轰动一时。由此致使了一场诉讼,一家动物福利机构向美国法院起诉,称作为拍摄者的猕猴应享有自拍照的版权,未经许可展现和出版照片的行动构成侵权,因此应当将侵权所得利润返还给那只猕猴,并制止他人今后再实行类似侵权行动。既然猕猴自拍照中的主角能成为“网红”,说明这张照片拍的不错,在情势上乃至与摄影师所拍照片难以辨别,那猕猴自拍照能否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对此问题的回答固然会不会定的。以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为例,《著作权法》第2条第1款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作品,不论会不会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第2款至第3款规定了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猕猴固然也是有智力的,否则也不会模仿摄影师的动作依照相机的快门。但是猕猴是“中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外国人、无国籍人”吗?固然不是。因此其“聪明才干”的成果不可能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更加重要的是,保护此类成果与《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不符。《著作权法》第1条清楚地阐释了立法目的——“为……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资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增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华……”。著作权法怎么实现鼓励创作的立法目的?其方式就是为作者设定专有权利,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这些专有权利就像栅栏,为作者的作品围起了一片专属领地,未经许可以复制、发行或交互式网络传播等方式利用作品就像擅闯他人领地,原则上构成侵权。因此他人如需以上述方式利用作品,原则上就要经过作者的许可并向其付费,由此使作者从他人对作品的利用中取得公道回报。作品的质量越高、越受关注,他人利用作品的需求越大,作者从中取得的收益就越多,其名誉也会日渐增长。
如此一来,作者有了继续创作的动力,同时也对他人,特别是青少年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这样的鼓励机制作用之下,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创作活动,从而增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华。明显,动物不可能遭到著作权法的鼓励,只有人材能理解著作权法并遭到鼓励,因此只有人的创作成果才能作为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这就意味着《著作权法》第2条所述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情势表现的智力成果”固然是指人的智力成果。美国“猕猴自拍照案”的诉讼也固然是以原告败诉告终,美国两级法院都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要求,理由是美国《版权法》只保护“人”的创作成果。

包括ChatGPT在内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固然也是如此,由于该内容也并不是人的创作成果,人工智能也不可能遭到著作权法的鼓励,因这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可能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在美国产生的“《通向天堂之近路》绘画登记案”中,一名叫泰勒的美国人要求美国版权局对一幅名为《通向天堂之近路》的绘画进行作品登记。泰勒宣称这幅画是其研发的人工智能在完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主生成的。美国版权局版权复审委员指出:“版权法只保护基于人类心智的创作能力而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美国版权局将不会登记在缺少人类作者创造性投入的情况下,由机器或纯洁机械进程而生成的内容”,因此终究谢绝对此绘画予以登记。在被称为“中国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第一案”的“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百度案”中,上述观点也得到了体现。本案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以使用法律统计数据分析软件(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生成的分析报告侵害其著作权。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自然人创作完成仍应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由于分析报告不是自然人创作的,……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仍以“猕猴自拍照案”为例,试问可否对照适用“视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作者”的规定,视那名照相机被抢走的摄影师为自拍照的作者,使其享有著作权呢?回答会不会定的。一样道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并不是由人创作,并不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此时固然也无所谓认定谁是作者,谁享有著作权。另外,在前文提及的“《通向天堂之近路》绘画登记案”中,作品登记申请人泰勒主张,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以根据美国《版权法》对雇佣作品的规定取得保护。这是由于美国《版权法》规定,对雇员在受雇期间为完成雇主的任务而创作的作品(即雇佣作品,类似于我国的职务作品),视雇主为作者,由雇主享有版权。美国版权局版权复审委员会指出,该观点不能成立,由于“雇佣作品以合同关系为条件,而人工智能不可能与人签订合同;同时《版权法》中雇佣作品条款关注的是版权归属而不是相关的内容会不会受版权保护。而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一定要是由人创作的。” 这也印证了有关拟制作者和权利归属的规定,与作品的认定无关。
辨别“人工智能生成的”与“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以作为作品遭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理由是该内容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或使用者以人工智能为辅助工具创作的作品。由于研发者或使用者是人,认定他们是创作者,就不会出现著作权法不保护非人类创作成果的法律障碍。在我国产生的第二起触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侵权诉讼中,腾讯公司认为他人擅自传播其人工智能写作软件Dreamwriter生成的新闻报导,侵犯其著作权。在该案中,法院认可“创作工具说”并认为:“涉案文章的生成进程主要经历数据服务、触发和写作、智能校验和智能分发四个环节。在上述环节中,数据类型的输入与数据格式的处理、触发条件的设定、文章框架模板的选择和语料的设定、智能校验算法模型的训练等均由主创团队相关人员选择与安排。……原告主创团队相关人员的上述选择与安排符合著作权法关于创作的要求,……应当将其纳入涉案文章的创作进程。……本院认定涉案文章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文字作品。”
笔者认为:审理该案的法院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谁研发了人工智能的算法、规则和模板?二是谁生成了构成涉案新闻报导的文字组合、遣辞造句?明显,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腾讯公司的主创团队”,但这其实不意味着对第二个问题也应当作出相同的回答。例如,人工智能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门,是从人工智能围棋程序(AplfaGo)克服世界冠军李世石开始的。但是该围棋程序的主要设计者只是围棋业余一段。计算机专家也指出,设计者们只需要晓得围棋的基本规则便可,其实不需要具有很高的围棋水平。李世石固然会承认自己在与人工智能程序的对决中,面对该程序精巧的算法和超强的算力败下阵来,但他恐怕不会接受自己的围棋水平不如主创团队,因此自己被主创团队打败的说法。因此只能说主创团队设计了人工智能围棋程序,但不能认为这盘棋是主创团队们下的,并认定他们克服了李世石。
对此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经修订的关于知识产权政策和人工智能问题的议题文件》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生成的’与‘人工智能自主创造的’是可以互替使用的术语,系指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由人工智能生成产出。在这类情况下,人工智能可以在运行期间改变其行动,以应对意料以外的信息或事件。要与‘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产出加以辨别,后者需要大量人类干预和/或引导”。既然腾讯公司将上述人工智能写作软件Dreamwriter生成的新闻稿称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固然属于在完全没有或基本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由该软件自动生产的。
结语:辨别应然与实然
前文得出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能作为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结论,是法律上的“应然状态”。但是这一条件是我们知道相关内容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在现实中,如果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或使用者并未表露相关内容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而是谎称该内容由自己创作并以作者身份署名。该内容只要在情势上符合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就能够作为作品遭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这是由于《著作权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以署名为基础的三项推定,即在相关成果情势上属于作品时,以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署名推定该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作者、该作品之上存在著作权,和该著作权归属于该作者。
由此就出现了与法律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辨别,实践中“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的辨别其实不是法律的缺点,更不能以需要保持两种状态的一致性为理由,而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认定为作品。首先,两种状态的辨别是正常现象且具有公道性。假定张三向好友李四借入1000元现金,未打借条。由于张三迟迟不还钱,李四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张三立刻还钱。试问法院应当如何裁判?理论探讨固然可以采取“上帝视角”,假定一切事实都清清楚楚,但法院审理案件一定要以证据为基础。如果李四不能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诉讼要求,法院只能判决李四败诉。因此,“以事实为根据”也是指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根据。换言之,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有时也会不一致。
其次,为了“定分止争”,保持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并以更低的本钱和更高的效力解决纠纷,法律常常需要进行推定,如上文提及的三个署名推定。但是推定可以被更强的相反证据所颠覆。在“《通向天堂之近路》绘画登记案”中,假设泰勒在人工智能生成的绘画上署名,称其为自己的作品并进行了作品登记。只要他人发现了这一事实(如他人用相同的人工智能程序生成了相同的绘画),该作品登记就会被撤消。
最后,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或使用者对会不会表露相关内容为人工智能生成的事实,常常进行过利弊权衡。在“《通向天堂之近路》绘画登记案”中,泰勒肯定知道只要不说该幅绘画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固然就可以够取得作品登记,也能享受版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比如通过许可他人利用此绘画而取得许可费。那末泰勒为何刻意选择宣称相关内容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呢?明显,泰勒希望借助申请作品登记(且知道该申请肯定会被谢绝)进行宣扬,即其研发的人工智能已能够生成高质量的绘画。但是此时名利不可兼得。泰勒借此取得了高度关注,但他一定要接受相关成果不能作为作品登记,自己也没法取得版权利益的现实,这对他而言并不是不公平的结果。
综上所述,以鼓励作品的创作为已任的著作权法,不会将包括ChatGPT在内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视为作品并提供保护,由于人工智能与猕猴一样,不可能遭到著作权保护的鼓励。此类内容也不能被解释为“视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作者”的作品,或人工智能的研发者以人工智能为工具创作的作品。某些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因人工智能的开发者或设计者谎称为自己创作的作品而遭到保护的现实,也不能用于反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理应遭到著作权法保护。至于不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作为作品保护,就会挫伤投资研发人工智能热忱的说法,更是缺少根据,由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常常会通过其他市场方式实现。
相关浏览
1.赵汀阳:GPT推动哲学问题了吗?
2.何怀宏:GPT的现实挑战与未来风险——从人类的观点看
商品书目


微信号 : DigitalLaw_ECUPL
探访数字法治逻辑
展望数字正义图景
战略合作火伴: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
tk账号购买:https://www.tiktokfensi.com/